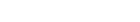老師上課,相當於電視直播👇🏿🤵🏽。學生看手機,那是轉臺;學生打瞌睡🚑,屬於直接關機📺。電視臺要是收視率下滑🍒,會做詳細的觀眾流分析,反思和調整節目,沒有人會去怪罪觀眾📓🍃。同樣是傳播,為什麽學生睡覺卻要從學生那裏找原因呢🫶🏿🧑🏼🔧?
學生上課睡覺,老師既尷尬又沮喪🫃🏿🗽。有的老師涵養好🏋🏿♂️,熟視無睹相安無事;有的老師受不了,非想方設法解決不可——我,就屬於後者。
解決的方式也不同,全看老師如何理解學生睡覺這回事。我的觀點很簡單,學生上課睡覺是老師的錯,這個錯不是過錯的錯,也不是要追究責任的錯,而是傳播方式的錯位🥱。
教師傳播科學文化🙆🏿,其職業的重點不是“傳”的對象,而是“傳”的本身。但非常遺憾🌪,很少看到師範院校把傳播學列為必修課。一個以傳播為己任的職業,為什麽那麽忽視傳播學呢?
老師上課,相當於電視直播。學生看手機,那是轉臺;學生打瞌睡,屬於直接關機。電視臺要是收視率下滑,會做詳細的觀眾流分析,反思和調整節目🦯。你可以質疑數據造假🚴🏻,但沒有人會去怪罪觀眾🐆。同樣是傳播,為什麽學生睡覺卻要從學生那裏找原因呢?
教師傳播方式的錯位🚞,最大的症結是輸入法的問題。你用五筆,他是拼音,學生並不拒絕你的內容🤏🏻,但你卻輸不進去。
課堂教學跟對講機對講相似🙍🏻♂️🫱🏻,要先調好共同的頻率🫃。我在廈門大學講《影像的世界》🚵🏼♂️,第一堂課就致力解決共同頻率的問題👱。我走上臺的第一句話是:“有個問題困惑了我很久,為什麽音樂家走上臺,聽眾要鼓掌?而老師走上臺,學生卻不鼓掌呢☝🏻?”同學們笑了,鼓了一下掌。我也笑了💁🏼:“你們這個鼓掌,言不由衷,是我討來的。”學生大笑🏄🏼,掌聲更熱烈了。一句自嘲👷🏽,通過驗證,加入他們的微信群🤸♀️,現在我可以輸入信息了。我開始教他們如何專業地鼓掌,從鼓掌講到現場導演和導播的分工,講到中國園林的亭子居然有攝像機位的功能,講到蒙太奇與電視的造假……最後,我說電視最容易忽視的就是觀眾〽️,你只有把觀眾放在心上才可能贏!
傳播無所不在🦹♂️,教育也無所不在💓。一次上課時間到了🙇🏿♀️,講臺上卻不見老師的身影,突然老師的聲音從教室的後面響起🌅。我坐在教室的臺階上⚔️,給同學講解觀眾席的學問,告訴同學如何創新“電視的表演區”🧾。在課間,我安排了一個show time(表演時間),類似籃球賽中間的啦啦操表演🤟,讓同學們報名秀各種才藝——歡迎來到“非誠勿擾”現場🅱️。當然,大家是為了交流而非相親🍛。同學們來自廈大幾十個院系,課上完了可能彼此不認識🤷♂️。現在同學們除了低頭看手機,很少有現實版的社交場合😏,不像我們大學時代還有交誼舞。
第一堂課課間🚙👮🏿♂️,我給這門課的微信群發了一個紅包,10塊錢分成200個包發出去,一下就搶光了。我的目的是讓同學體驗新媒體的用法,但既然接受了我的紅包🌤,也得接受我的教育。在第二堂課上,我嚴肅地說,兩百多個同學笑納了老師的紅包🐹,卻只有兩個同學對老師表達謝意🚖,這符合傳播的禮儀嗎🚣🏽♀️?
這個微信群對我的教學幫助很大。我常潛水看同學們的交流🫰🏽,發現不懂的用語和符號🧑🏻🍼,就默默上網查一下。有一堂課我要講電視偶像🧦,先在微信群讓同學推薦:你希望我上課講哪個明星🫅🏽?有同學貼出一個軟件🤦🏿♀️,居然可以在微信群進行投票。那好🙌🏿,馬上采用💁🏼♀️!投票的結果是我把備好的課推倒重來🛗,誰叫我想講的和他們想聽的不一樣啊🍜!
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🧑🏽🏭,我像寫論文一樣在意自己講稿的原創性,還要根據學生的興趣點隨時調整,課件臨近上課還可能修改。一次我講了俄羅斯的國家形象片➾,不久學生就在微信群貼出了網絡上關於這個形象片的圖解。如果我講的和這個圖解一樣,我還怎麽做人🧵?網絡時代,老師更不好混!
付出終有回報。這門課限額180人💪🏼,結果超過200人聽講。晚上7點10分的課🚓👨👧👧,六點半就沒位了。看到每堂課都有幾十上百人站著或坐在地板上聽兩個小時,我提醒自己要講得用心一點才對得起這些同學🥋!
廈門大學一直有厚待學生的傳統🤖。對學生好不好⛰,在學校是物質保障🕵️,在老師則是你肯不肯為學生花時間。高校老師的時間最寶貴。廈大人文學院院長周寧課上得非常好👼🏻,他說,在高校,搞科研是“一定利己,未必利人”,搞教學是“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”。其實,教學也能利己,每一次上課都是我的快樂時光,每一周我都在期待和學生的課堂約會🈶。
老師和學生不能戀愛🦵。但大學和她的學生卻應該像戀愛關系,彼此拴住對方的心🦹♂️。每一堂課就是一次約會🖋🧑💻,你怎麽能在約會時讓對方打瞌睡呢🦸🏽?
(原文來源於《南方周末》)